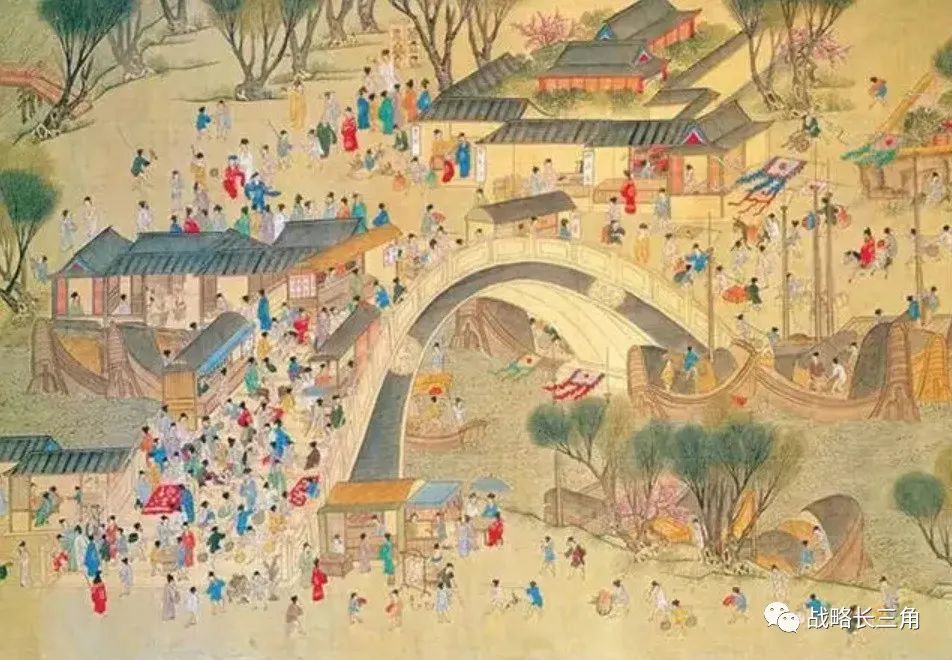果说上海因开埠走上T台翩然起舞的话,那么千余年江南文化的浸润则是涵养筋骨积蓄能量。自隋唐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倾斜东南,江南文化得以发展,至明清形成以长三角区域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处于江南腹地的上海正是在此间蓄能滋长的,除了地理交通和水陆物产外,其人物特质也是破解其日后腾达的重要原因。近代上海的发展得益于移民的到来,那么明清上海人口的组成与来源具有怎样的特质,可否找到其日后繁荣兴盛的人物密码?
一、明清上海士人群体的籍贯都在哪里
明清时期我国还没有完备的人口统计体系,部分人口信息一般通过家谱、户口册等资料进行收集,所搜集的资料具有较强的个体性,对一个地区某一群体的人口信息尚显不足。笔者在探究我国传统丧礼的过程中发现,传统墓志自魏晋南北朝成熟定型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特例,内容包括墓主的生年、籍贯、世系、婚姻、生育、卒年等,这为我们了解古代人口信息打开了一扇窗户。当然,由于经济条件与知识文化的限制,传统社会中能制备墓志的一般属于士人知识群体,所以该人口信息一般仅限于士人群体。该群体虽然不能代替所有的社会阶层,但因其掌握文化资源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到引领的作用。
那么,明清上海墓志所反映的士人群体究竟具有怎样的组成?外来移民占有多大的比例?其籍贯又来自哪里?五百多篇明清上海墓志的记录为我们揭开了这层神秘的帷幕。鉴于传统墓志对男女墓主的不同记录体例,我们选择男性墓主作为分析样本,因其世系、籍贯记录是必须的。根据样本统计,在总人数457人中,上海本地籍贯的人数为314,占比为68.71%;非上海籍贯的人数为143,占比为31.29%。由此可见,明清上海士人群体以本地人为主,约占总人数的68.71%,由外地迁入上海的比例占到三成多,是很高的迁入比例。
从墓志统计来看,迁居上海地区的士人来源涉及十四个省份地区,主要有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西、河北、四川、新疆、山东、福建、湖北、陕西、广西等地。从非上海籍贯地域分布占比来看,由河南迁居的人数最多,占迁居总人数的32.68%,其它占比在10%以上的地区分别为浙江、江苏和安徽,其占比分别为19.75%、16.67%和14.2%。其余十个省份迁居人数占比均在5%以下,其中江西为4.32%,山西和福建占比均为3.09%。
在外来士人中,来自河南的最多,其主要原因是受“衣冠南渡”的影响。此外,浙江、江苏和安徽的迁入比例较高,因为这三个省与上海在明清同属江南核心区域,也就是现在的长三角地区,区域内的人口流动相对频繁在统计数据中也得到了反映。江西部分地区也属江南核心区,其迁入上海人数仅排在安徽之后,这也反映了江南文化圈内部的人口流动相对较多。从地域人口流动来讲,福建与上海的关系比之山西更为紧密,而统计数据则显示,山西与福建迁入上海人数比例持平,这反映了明代山西移民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其它地区有较小的迁入比例,除了个别原因没有形成显著的因果关系。
二、移居上海的原因分析
上海地区的发展伴随着人口的集聚,特别是士人群体的壮大更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上海能够吸引不同地区的人们来此定居,有其一定的地缘与经济优势。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多为墓主祖上移居上海,其中有衣冠南渡的、有避乱求安的、有因官移家的、有乐此风土的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少数由于婚姻、生存等原因造成墓主本人移居上海的情况。
1.衣冠南渡
上海史大家熊月之先生指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得益于持续的开放与交流。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与宋代靖康之乱,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迁移。北人南迁不是难民零星迁移,而是包括统治阶层、名门望族、士子工匠在内的集群性迁移,是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在内的整体性文化流动,即所谓“衣冠南渡”。墓志统计迁居上海的以河南士人最多,不难看出“衣冠南渡”对上海的影响。
明代墓志中,如《明故迪功郎顺德府知事潘公(誉)墓志铭》录:“……世居河南,随宋南迁,遂占藉于苏之嘉定焉”,《奉贤明儒学生王廷璧墓志铭》录:“……其先汴人宋王晋公之裔,八世祖始迁于松江之华亭”,《前明锦衣卫左所千户屯田都司王翁子万墓志铭》录:“……翁十七世祖某,其谱称富一公,为宋崇政殿说书,南渡家于松江之上海,遂着籍焉,世为衣冠之族”;《明故文林郎署兵部车驾司郎中事行人司司正前四川道监察御史韦室唐公(自化)墓志铭》录:“……宋建炎中,始祖将士郎贵一,扈宋高宗南渡,卜居华亭之白砂里”。
清代墓志中,如《施维翰墓志铭》录:“……先世居汴梁,靖康末,南渡居松江,遂为上海人”,《左都御史朱椿墓记碑》录:“……其先故洋人,从宋高宗南渡入淛,徙居松江之上海,再徙沈庄,其卜宅娄西门而为其县人者,自公机考始”,《广西巡抚李公神道碑》录:“……公讳锡秦,字瞻仲,号砚农,江苏直隶太仓州宝山县人。其先世系出庄渠公,自宋南渡后,世居胡家庄”。
从以上墓志举例中不难看出,在明清上海士人家族中,其先世因靖康南渡迁居到此的还是较为普遍,这种普遍性也是外来士人籍贯多为河南的主要原因,而“衣冠南渡”的士人无疑为上海的蓄力发展埋下了文化的种子。
2.避乱求安
上海偏居海隅,并远离政治中心,因而成为避乱求安之地。明代墓志中,如《孙承恩墓志铭》载:“……其先在南宋除自河南开封迁居杭州,元末避乱迁居华亭”,《永嘉张氏世墓表》载:“……张氏其先永嘉人,先生曾祖讳斌,元末避乱携其室陈氏渡浙江,居华亭之南桥镇”,《友竹处士胡君墓志铭》载:“其先家平湖,元季兵乱,自戈溪徙华亭界泾南,遂为华亭人”。
清代墓志中,如《清修孔宅衣冠墓碑记》载:“接青邑令李若元牒及《云间志》:郡北六十里,地名孔宅,……考其故,盖自至圣二十二代孙、后汉太子少傅讳潜,避地会稽,遂为郡人。”该墓碑记录了孔子后代的迁居情况,早在后汉时期,就有第二十二代孙名孔潜的为避祸来到会稽地区。
3.乐吴会风土
上海地区有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环境优美,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明清期间,有许多人就是由于喜爱吴会风土而迁居上海,如《处士南溪朱公墓志铭》所录“焘官饶州教授,又为饶州人,自饶州又传五世,讳素者,仕元,为松江府推官,乃乐华亭风土居之,故今为华亭人”,朱南溪即因其祖上乐华亭风土居之而成为华亭人的。又如《故处士陈汝敬墓志铭》所载“处士讳钦,字汝敬,号持谨,晚号敬庵。其先世居庐陵。自曾祖茂林,喜嘉定川流如练而萦回,林壑尤美,乃择守信乡居焉”。嘉定人陈汝敬籍贯为江西,其先世喜爱嘉定川流林壑而徙居练川(嘉定又名)。再如《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记载“……君固乐南翔风土,而其为人有惠爱,虽南翔亦惟恐其不留也。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
4.因官移家
官宦属较高层级的士人群体,其作为封建国家运作的重要力量,是要根据国家的需要而到不同地方任职的,因此,官宦家族迁移成为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许多人就是由于在上海地区担任官职而将整个家族迁居到此的。
明代墓志中,如《故泾府右长史致仕任先生墓志铭》载:“元安定书院山长松乡先生士林七世孙,明福建参政薇庵先生勉之之孙,而执庵处士弘之子也,松乡子耜为两浙盐运照磨分司松江,因家焉,故今为华亭人”,《副千户唐公墓志铭》载:“唐氏着上海,上海之唐寔出子方,晋阳灵石人也。吴元年,有讳英者,官乌泥泾税课局大使,因家焉”,《廷评姜君墓志铭》载:“君姓姜氏,讳岐,字希文,号桂楼,先世汴人,逺祖伯宁仕宋阶武畧将军,十世祖文辅元时为溧阳州经歴改松江府知事,遂占籍华亭县”。
清代墓志中,如《华卿公墓志铭》载:“君姓廖氏,讳文耀,字画庭。华卿,其号也。先世福建永定人。曾祖讳冀亨,官江苏吴县,以清介忤噶礼,罢职。祖讳鸿章,乾隆丁巳进士,官翰林,掌教紫阳书院。考讳守谦,寄居嘉定,遂家焉。”华氏本为福建永定人,因其曾祖父在江苏吴县任官、祖父掌教紫阳书院,最后在嘉定安家定居。
5.姻亲安家
在明清士人家族中,有一些是因为婚姻关系或者投靠亲戚而迁居到上海的。如《明吴淞江守御所千户施武略室宜人钟氏之墓志》记“钟氏者,温州府永嘉县中界山元朝元帅钟择美之女也。未笄,明州卫百户施承信为长男求聘焉,亲迎过门,既长毕姻。洪武二十八年,夫升吴松江千户。”钟氏即是通过婚姻关系,随其夫而安家于松江。投亲也是迁居异乡的一种原因,如《外舅光禄寺典簿魏公墓志铭》载:“公讳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吴葑门之庄渠,依其姨母,因从其夫姓为魏氏而居昆山之真义。”可见,为了生存,即使是投靠姨母,也要随从姨夫而改姓。
6.其它原因
除上述几种主要原因外,移居上海还有一些其它原因。如《诰封太恭人顾氏墓志铭》记“……太恭人系出浙之鄞,以有戎籍于松江所,故今为华亭人”,显然,这是因为从军而落户松江。再如《絅庵姚先生墓志铭》载:“世荣之后皆以善医名,有桂发者,尝起安定郡王伯栩竒疾,授御医局副使于先生,为七世祖,子垕,号朴翁,以名医被荐赐冠带,由临安徙华亭,居修竹里,子文彬,号恒斋,元惠民局生,累官医学教授,与鐡崖杨先生为诗友,其葬也,鐡崖志之。”从中可知,姚氏七世祖因为医术高明而被荐赐冠带,由临安迁居华亭。